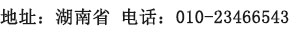豆瓣酱,即俗称的“胡豆瓣”,古来蜀中多地有造并作为当地土产。清光绪《郫县乡土志》载:“胡豆瓣,川人常鬱[yù]豆瓣去性,和椒以盐渍之,咸辣异常,以佐食味。”民国《简阳县志》载:“豆瓣酱,胡豆和海椒制。”海椒,即辣椒。因辣椒为酱中主料,故豆瓣酱亦称“辣豆瓣”。清时,蜀中辣豆瓣即名声远扬,时见于宴席之中。晚清学者、江浙人氏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抄》中记载:“今日为黄荛翁百五十岁生辰,……席有蜀中辣豆瓣。”
食用酱,早在先秦周时即有记载。《周礼·天官·食医》载:“凡食齐眡[shì]春时,羹齐眡夏时,醬齐眡秋时,饮齐眡冬时。”汉·郑玄《周礼注疏》载:“酱,即豆酱也。”豆酱制作,历史久远。豆类蛋白质会在曲霉菌作用下分解并产生多种酶,而这正是豆酱形成及其风味突显的重要原因。豆酱,多以大豆,亦称黄豆,为主要原料。明·韩奕《易牙遗意》中记载有豆酱的做法:“豆酱,用黄豆一石,晒干拣净去土磨去壳,沸汤泡浸候涨,上甑蒸糜烂停如人气温,拌白面八十斤,……摊芦席上约二寸厚,三五日黄衣上,翻转再摊罨[yǎn]三四日,手挼碎盐五六十斤,水和下缸拌抄,上下令匀……”
豆酱佐餐,不仅生津开胃助消化,而且富有营养。古人十分看重豆类食物。清晚民初《清稗类钞》载:“豆类为大豆、小豆、豌豆等,皆富蛋白质,大豆所含之脂肪多于牛肉,故为廉价滋养品中之第一。豆腐、豆酱均属滋养之美品,且易消化。”民国《叙永县志》载:“大豆,即黄豆,富于滋养料,他物无有能比拟者,凡豆腐、豆乳、豆油、豆饼、豆酱、酱油,均可制造。”
豆酱制成后,酱中保持着瓣状的黄豆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口感和味道。当人们有意识地采用保留或添加豆瓣的方式制酱,早期的豆瓣酱于是就产生了。可以说,豆瓣酱是在偶然的发现中发明出来的。一些古籍中透露出的零碎信息表明,至少在金元时期,已经有了豆瓣酱的成熟做法。例如,元《金史》载:“酱瓣桦者,皮斑纹,色殷紫,如酱中豆瓣也。”马齿苋,又名酱瓣草,盖因马齿苋的叶片状如酱中黄豆瓣。明《汝南圃史》载:“马齿苋,一名五行草,以其叶青茎赤根白花黄子黑而得名也。其叶似豆瓣,故吴俗又呼为酱瓣草。”清同治《新宁(今开江)县志》载:“马齿苋,一名酱瓣草,皆野生。”酱瓣之称,显然指的是酱中的黄豆瓣。
胡豆,也称蚕豆。以胡豆或蚕豆为原料制作的豆酱,出现较晚。从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,胡豆瓣酱,在清代中后期才渐有记载。有关胡豆瓣酱的做法,大同小异,不仅四川,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制作胡豆瓣酱的习惯。清光绪《广安州新志》载:“酱,以豆麦蒸为饼,阴寘[zhì]使干,煮药水和香渍之,重以盐,值三伏日晒之,饼融为屑,至立秋节置瓮中,味香浓,清者为油,故家重伏酱秋油,以蚕豆析瓣置其中,曰豆瓣酱。”民国《西乡县志》载:“胡豆拌辣子制成者,曰胡豆瓣酱。”民国《吴县志》载:“以蚕豆瓣和以面麸,拌以盐水,经日曝之而成,曰霜降酱。”
清光绪《黎里(今属江苏吴江)续志》中还有胡豆瓣酱制作的详细介绍:“蚕豆一升,用干面一十六两,择初伏始热之日,将蚕豆剥去青衣煮烂,以干面和匀扭透,制成糕式,切作小方块摊至筐内,微覆稻草,闭于室中,须择干燥无风之处,约七日即成黄子,以出毛为度,其毛愈长愈妙。其制酱法,凡黄子一十六两,用盐五两五钱,水一十二两,同储坛中,粘蒻封口,置向阳屋上,约晒一月,自然成酱,即可取食。”该续志中所记载的做法,与今四川地区豆瓣酱之“翻、晒、露”的做法,几近相同。
▲郫县豆瓣博物馆里的酱缸
▲成都川菜博物馆里的酱缸
谈及胡豆瓣酱,这里还要特别地说说胡豆。
胡豆,古名戎菽。清《公羊义疏》载:“戎菽,谓克戎之菽。齐侯此时克山戎并得胡豆。”清《尔雅义疏》载:“戎菽,布之天下,今之胡豆是也。”据宋《太平御览》载,胡豆为西汉时由张骞引自西域,即“胡人之地”。胡豆,或蚕豆之来源与得名,也有其他说法。明·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载:“戎菽,蜀人所谓胡豆也,志云,蜀人得种于羌戎故名,又云,即蚕豆。”明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蚕豆,释名胡豆,豆荚状如老蚕,故名。谓其蚕时始熟故名。”胡豆,也常写做“葫豆”。清乾隆《中江县志》载:“蚕豆,荚如老蚕,故名,即葫豆也。”清光绪《永川县志》载:“蚕豆,俗呼葫豆。”秋播春收,胡豆为一年生越冬植物,元·王祯《农书》载:“蚕豆,百谷之中最为先登,蒸煮皆可。”因其具有耐寒特性,一些地方则称胡豆为“寒豆”。
据记载,胡豆大约在明代中期由云南引入并广泛种植于四川各地。清嘉庆《金堂县志》载:“蚕豆,亦名寒豆,俗名胡豆,成化中邑令何泰自云南携种来。何泰,云南举人,成化中任,贤声远著,尝携蚕豆以遗民,自是广播原野。至今咸食其德,崇祀名宦祠。”明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蚕豆,南土种之,蜀中尤多。”
胡豆也被称为“佛豆”。宋·宋祁《益部方物略记》载:“佛豆,豆粒甚大而坚,农夫不甚种,唯园中莳以为利,以盐渍食之,小儿所嗜。”清·刘宝楠《释谷》中解释:“宋祁佛豆一类,秋种春敛,此即胡豆。”若宋祁所称之“佛豆”即后来所称的胡豆的话,宋代时蜀地就已经种植胡豆了。当然,前后的品种可能是有差别的。
胡豆耐寒,亦喜温湿环境,农人常栽种胡豆于田塍地边,或房前屋后的隙地。也有成片大面积种植,以及与其他农作物间种的情况。四川多地的一些地名,保留着旧时种植胡豆的历史。例如:胡豆湾、胡豆坪、胡豆塝、胡豆冲、胡豆咀、胡豆沟、胡豆园、葫豆坝、葫豆山、葫豆田、葫豆地、葫豆塆、蚕豆湾,等等。旧志中关于胡豆的记载很多。清嘉庆《犍为县志》载:“蚕豆,一名胡豆,霜降种清明熟,农家呼为小春,最赖之。”清嘉庆《什邡县志》载:“胡豆,一名蚕豆,大小二种,先百谷熟,可接新,九十月种多,宜谷田收后,不碍插秧,叶可代粪,子可熟食。”土质与种植方式,对胡豆的生长及其特质有一定影响。清咸丰《资阳县志》载:“邑种蚕豆,以城中者良,皮薄实粉,入市人争货之。”清同治《理番厅志》载:“蚕豆,俗名胡豆,杂谷产者大而白。”清光绪《资州直隶州志》载:“胡豆,资土最宜,农人收获后即种之,以备春粮。”清光绪《简州续志》载:“胡豆,一名蚕豆,城南花园地种者,色白皮薄而大倍常,易地则变。”民国《潼南县志》载:“大蚕豆,产县属下县坝,较他处所产为巨,远近争购之。”
▲长满曲霉菌的胡豆瓣图片来源于网络自引入起,胡豆就是四川地区常见的杂粮,人畜皆可食用。民国《三台县志》载:“蚕豆,可作酱作豉,又有以之饲牛马者。”关于胡豆的种植与食用,民国《重修广元县志稿》中有很详细的介绍,志云:“蚕豆,俗称胡豆,一作佛豆,乃豆科越年生草本农作物。晚秋下种,入春长成,苗高一二尺,方茎中空,羽状复叶,小叶椭圆形,叶腋开紫色蝶形花,三月成熟结荚果,内藏大粒种子三四枚,即胡豆也。本县各地均产之,用途亦广。除直接佐食外,常用于制豆瓣酱,又可磨为胡豆粉,用以浴面能去垢。其种子嫩时,俗称嫩胡豆米,和米为炊,尤饶香味,嫩叶亦可轧酸菜为食。”
胡豆,与大豆一样,蛋白质含量高并富集多种微量元素,可新鲜食用,也可晾晒干后储藏备用,故很受人喜爱。旧时不少地方还专设有售卖胡豆的市场,例如清嘉庆时期,汉州(今广汉)城中即设有“葫豆市”。一些地方胡豆及其制品的销售,也颇有规模。民国《简阳县志》载:“胡豆,岁约销二千石,饲牛马,作酱料。酱品,惟豆油、麦醋、胡豆瓣、麦酱,城内及各场岁约售货钱四万串。”
自古以来,酱,一直是食作中常用之品,也是佳肴上品。唐·颜师古《急就章注》载:“酱者,百味之将帅,酱领百味而行。”以胡豆和辣椒为原料制成辣豆瓣酱,当是胡豆食用的经典之作。清晚民国时期川菜味型的最后形成,与辣椒和辣豆瓣的普遍食用不无关系。清代晚期,四川多地生产豆瓣酱,豆瓣酱成为了当地的土产特产。清晚民初文人傅崇矩编著的《成都通览》中,所列清宣统年间劝业会送展豆瓣酱的地方就有犍为县、南部县、邛州、温江县、眉州、郫县、彭山县、成都县、通江县、射洪县、雷波厅、合江县、青神县、资阳县、巴县等。各地之豆瓣酱的名称叫法也是多种多样,如豆瓣、酱瓣、酱豆瓣、豆瓣酱、胡豆瓣、胡豆酱、辣豆瓣、黑胡豆瓣、红胡豆瓣、五香胡豆瓣等。由此可见,至清末时,豆瓣酱已成为四川地区家喻户晓、人皆爱之的佐餐之物。实际上,那时的普通人家几乎都有制作豆瓣酱的习惯。清晚时期,生产豆瓣酱的一些名家大号渐渐形成并驰声走誉,例如郫县的“益丰和”、彭县的“元丰源”等,其中一些商户因其酱质好味道佳而产销两旺,进而成为当地富豪。清光绪《郫县乡土志》中记载:“邑有陈姓酱园所造最佳,远近驰名,凡官商之经郫者,必多购之,归以相馈遗,而陈因以致富。”
▲《郫县乡土志》内页
保持着传统风味的豆瓣酱,备受无辣不欢之川人的喜爱,从古至今。正是因为有着大众的喜爱,豆瓣酱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,相应地,文化传承也就有了稳固的基础。
相关阅读追本溯源巴蜀风物博考川主庙
薅草锣鼓
农乡赛会
鸡公车
水碾
竹器
林盘
火井
石桅杆
豆花
茶馆
腊八粥
投稿邮箱:bashufengwuzhi
.